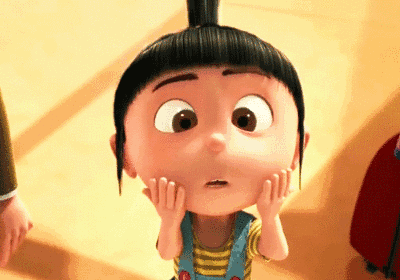01新政诱发革命
革命之前有一场晚清新政,用今天的话说,叫改革,就是统治者自身进行的制度改革。革命的遗嘱总是由刽子手来执行,戊戌变法虽然被慈禧太后一个巴掌打下去了,但是到了1900年以后,八国联军打进来,最后签订了耻辱的《辛丑条约》,慈禧太后知道不改不行了。
开始是清廷的自我变革,1901年开始晚清新政,到1904年以后开始加速,因为1904年发生了一场日俄战争,这场战争竟然是日本人打败了老牌的俄国帝国——黄皮猴子打败了老牌的北极熊。当时舆论总结说,这是立宪国打败了专制国。日本已经开始民主维新,君主立宪,俄国还是个专制国家。
于是大家说,主要因为日本的制度好,立宪是先进的,专制是落后的。1904年后,整个中国开始有了强烈呼声,要求立宪,所以晚清新政在1904年后开始加速,特别是到了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2005年科举废除一百年的时候,我在《文汇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没有05,何来11》,也就是说,如果没有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很有可能没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
最早发动武昌起义的是新军中的青年军官。这些青年军官本来都是要考科举的,但科举制度废除后,精英们开始分化流向社会。
这些精英各奔前程,经商的经商,搞教育的搞教育,还有一批人开始从军。晚清舆论认为军人很光荣,而且要振奋武力,军事救国。大批有为的年轻人开始从军。当时到军事学堂读书,是很时尚的事情。
周作人晚年写回忆录时也很得意地写上一笔,说早年也曾当过海军。从军中的一批人,后来又到日本读士官学校等各式各样的学校,然后带回来满脑子的革命思想和现代化思想。他们到了新军之后都做了青年军官,当然不满意当时腐败的体制。“没有05何来11”,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跟科举制废除有关。
事实上在革命发生前的十年时间里,中国在变化,社会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变。各种教育制度改革、企业制度改革,商会成立,法律改革,各种改革都已经开始,而不是一团漆黑,一片沉闷,革命也不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改革以后这个制度似乎在慢慢变好,但竟然发生了革命。这场革命是一场由新政诱发的革命。
02新政造就了三股政治力量
新政是一场改革,但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改革如果迅速彻底,它将是革命的替代物,万一改得不好,改得不彻底,那就是革命的诱导剂。晚清新政由于它的不彻底,恰恰成为了一个革命的诱导剂。
新政造就了几股新力量的产生,改革是一场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重新分配。一些阶级起来了,一些阶级下去了,一些阶级崛起了,一些阶级消解了。新政主要造就了三股新的政治力量。
第一股是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潜伏于体制外面的革命势力。这批人用传统的话说,不叫革命者,叫游士和游民。通常到了王朝末年的时候,在体制内就会有一批人被抛出来,成为体制所不能容纳的游民。会党就是一批游民,但游民自身不能成事,要有读书人来引导,读书人就是游士,也是游荡在体制外的。
恰恰是这两股力量合起来,就是会党(游民)和革命派(游士)。革命派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是读书人。这批游士不是传统的游士,而是满脑子革命思想的游士,这股力量虽然平常看不见,但潜伏在民间。
第二股力量是在体制边缘的地方士大夫精英。这批人就是太平天国以后出现的一股力量。明末士大夫很活跃,比如东林党、复社,成群结队建立各种结社,然后向朝廷提意见。这就是清议。复社当时在苏州虎丘塔下集会,竟然有一万多人。
清朝以后就开始压抑士大夫力量,觉得这是一股很可怕的颠覆力量。整个清朝士大夫大都是犬儒,考科举的考科举,要么就是做考据。但是到了太平天国以后,地方的精英开始崛起,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名,这批士大夫精英可以拥有湘军、淮军等地方军队,自己有税收厘卡。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这股力量已经尾大不掉,各省的这批士大夫精英说话非常有分量。晚清以后各种各样的改革,都是由地方自下而上开始的,而不是从中央开始,这和俄国革命、法国革命都不一样。地方的士大夫精英就是当时从洋务开始改革的核心,在改革当中,特别是到了晚清新政,虽然也是由朝廷颁布的新政,但整个动力都在地方。
美国学者周锡瑞对辛亥革命的经典性研究表明,晚清新政只是属于上流社会的变革。精英阶层在新政中拿足了好处,利益大大扩张,各种新政都是由精英来办的,包括办教育、办实业,其中有各种新的资源、新的好处可以分享,精英在整个新政当中都是既得利益者。
但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却要让底层社会来承担,广大民众就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普遍对新政不满,民怨沸腾,民众当时对新政有一股强烈的反弹力量,这股力量也就成为后来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
按照中国历史的政治传统,士大夫是惟一具有政治特权的阶级。老百姓莫谈国是,士大夫可以参政议政。士大夫是否和朝廷同心同德,这很重要。这场晚清新政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太强大了,在人心当中唤起的是一股前所未有的人性之恶——私欲、欲望的力量。
希望占有更多物质,从而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力,所以在新政当中获得好处的精英们,并没有因为已经在经济上捞足了好处而满足。他们在立宪这样一个新观念的号召下,特别是看到立宪国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他们开始希望从一个经济上强大的阶级上升为一个政治上强大的阶级,也就是说他们开始要和清帝分享权力。
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士大夫们开始政治化。而这个时候清廷由于搞新政需要地方精英参与政治。清廷从1906年开始被迫筹备立宪,准备用九年的时间筹备立宪,在立宪前首先要开始地方自治。
1909年通过选举产生了各省咨议局,过去非常分散的士大夫开始有组织了,地方士绅们的政治参与得以组织化,在体制边缘形成了一股正式的、合法的政治力量。这些地方精英的政治胃口开始大增,不满清廷九年后立宪的远期承诺,发起三次请愿运动,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尽早立宪。
法国大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指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人们耐心地忍受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被革命摧毁的政府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要好,一旦开始变革,苦难就开始变得不可忍受。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这个定律也完全可以用来说明晚清。
第三股力量是体制内部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势力。在晚清,北洋代表着改革派,是正面人物。特别是袁世凯,如日中天,是国家重臣,几乎所有晚清的新政都是他推出的,他当时代表着一个改革的形象。
北洋是新政改革的有力推动者,在新政当中也是捞足了好处,通过编练新军,整个北洋成为当时最大的实力派,也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清朝的最后十年,他们在权力中心日益坐大,掌控了国家军事、经济命脉,尾大不掉,成为清廷担惊受怕的异族势力。
当慈禧去世,小皇帝溥仪即位,清廷第一件事就是将袁世凯打入冷宫,“回籍养疴”。袁世凯虽身处乡野,却时刻窥探着局势变幻,准备有机会东山再起。虽然袁世凯被削下去了,但北洋这股势力还在,还是他的人,都是他小站练兵带出来的,这股力量具有极大的颠覆性。
晚清清廷迫于形势搞新政,但是改革也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释放出了三个魔鬼,这三股力量释放出来后,就再也收不回去了。用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话说,这叫做“参与爆炸”。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当中,由于社会流动的加强,就会形成参与感的加强,最后会形成“参与爆炸”,就是很大的政治参与的压力。
这个时候,它会考验统治者的智慧。倘若统治者明智且有魄力,当顺应时势,通过立宪,将新政所释放的动力,引入宪政的池子,让他们到国会里面去相互竞争,从而以制度转型的方式保持秩序的稳定。
然而,气数已尽的清朝最后一代统治者,敢于搞新政,却没有勇气开放政权,面对日益高涨的参政压力,最后来了个倒行逆施,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以垄断权力。这一下激怒了所有被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不说民间的反满势力,即便是温和的士绅阶级和权力中心的北洋势力,也从此心怀异心,谋求突变。
对新政最不满的人是各省的士大夫精英,他们本来希望朝廷能顺应潮流开放政权,提前立宪,搞国会选举,结果却来了个皇族内阁。地方士大夫精英的领袖是南通人张謇。他在南通办纱厂搞实业,是江南士大夫的精神领袖。
张謇和汤化龙等人领导了三次请愿运动。他虽然过去和袁世凯关系一般,但竟然放下架子,在去北京的途中到河南拜访了袁世凯。等到武昌起义一发生,清廷马上召集袁世凯,要他率领北洋军去讨伐。袁世凯推三阻四,张謇一开始还是希望能镇压革命,后来发现这股势力开始弥漫开来,决定转向革命,张謇所代表的这股核心力量开始背弃朝廷。
这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一个转折。清廷这才如梦初醒,马上宣布立即召开国会,实行虚君共和。
清廷公布了“十九条信约”,宣布立即实行责任内阁、颁布宪法。原来立宪派提出的条件只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十九条信约”索性更进一步,是英国式的虚君共和。虚君共和虽然保留了清帝为君主,但他只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性权威,而且其权威性不再来自天命,而是宪法,国家的权力转移到了议会以及由议会所选举的责任内阁。
但是,这个方案竟然没有被接受,这个方案假若被接受,很可能就没有民国初年的乱局。三股力量中没有一股力量愿意接受这个方案。
为什么会放弃这个方案呢?这和中国传统的观念有关,中国的士大夫们受到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影响,他们太崇拜权力了,以为权力就是权威,权力与权威在中国古代是合二为一的,皇帝既有权力又有权威,但是这两者并非同一。
权力是统治者的控制能力,权威是被统治者所认同的自愿服从的统治。二者在中国古代皇帝身上合二为一,因为皇帝是天子,中国古代最大的权威是秉承天命。当然,在中国古代政治里,权威也不是只有皇帝才有。按照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权威学者张灏教授的说法,中国古代政治有双重权威,一重在皇帝那里,另外一重在士大夫精英那里。
皇帝掌握了政统,士大夫掌握了道统和学统。张謇这批人考虑的是天下不能乱,寄希望的不是制度性权威的和平演进,而依然是一个可以安定全国的权力中枢。过去他们将目光投在清廷身上,如今见旧主大势已去,便转向了实力派人物袁世凯,于是在共和的名义下导演了一出“非袁不可”的斡旋戏。
“十九条信约”如果能够实践的话,它是一套制度,人不重要,清廷只是个虚君而已。但立宪派这些人太短视了,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他们还是迷信人的力量,错过了从人治转向法治的历史时机。
03恢复权力的秩序,还是权威的秩序?
民国初年面临的最大历史使命是建国,要建立一个中华民国。建国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秩序的危机。新的秩序首先要恢复权力的秩序和权威的秩序,这两个秩序都有待于尽快地恢复。
重建权力中心和国家权威,这是两条不同的建国道路:第一条路是迅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权力,通过强有力的力量来控制地方、民间、社会、舆论,当然秩序就会恢复。第二条道路是重建权威,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以制度作为权威,大家服从这个制度也可以形成一种稳定的秩序。
通过权力来重建秩序是最快最见效的,但是它会留下众多后遗症,表面上看起来一片稳定,但后面很多制度问题都没解决。但是通过制度来重建权威,又会比较漫长。
这两条道路不妨理解为法国革命的道路和美国革命的道路。
法国革命以后,依然围绕着权力来建立秩序。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首先是立宪,围绕制度来建立秩序。民国初年,从辛亥革命发生的形式来说,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这很像美国革命。但是民国成立后,却偏离了立宪建国的道路,而是开始学法国,三股力量:革命党、立宪派和袁世凯各派转而争夺国家最高权力。
他们围绕的核心问题,都是要争夺最高的国家权力。民国初年各种论争,都与此有关。第一个大的争论是,民权至上还是国权至上?民权的背后实为地方权力,国权的背后则是中央权力,民权和国权之争,反映的是以地方权力为中心还是以中央权力为中心来建立新的共和体制。
当时同盟会已经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代表着地方的民主派和实力派,它不愿意看到以袁世凯为中心的中央权力太强大,所以强调民权至上。而清末的立宪派改组为进步党,他们希望重建中央的权威,觉得民国初年各省势力太大了,国不成国,要迅速建立中央权威。他们要拥护国权,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另一个争论是,究竟采用内阁制还是总统制?国民党是国会内部第一大党,宋教仁(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坚持搞责任内阁。而进步党作为少数党,则希望借袁世凯的势力平衡国民党,希望搞总统制。民国初年的党争非常厉害,国会里边就是国民党和进步党在那里斗,争夺的核心就是要拼命扩张自己的权力。
袁世凯则以“临时大总统”超然于党争之上,反而渔翁得利,上下其手。按照原来临时约法的规定,总统任免地方官员要总理副署,没有总理副署,总统任免是不生效的。袁世凯在双方斗得正厉害时,不经总理副署,开始罢免省长,任用自己的人。
如此明显的违宪之举,不仅借袁世凯自重的进步党人没有反应,连国民党议员也没有反应,居然让袁世凯得逞了,因为他们都没把临时约法当回事。所以,袁世凯就一步步通过破坏制度来实现总统独大。
民初政治的重要转折点是宋教仁被刺杀。宋案之后,各种证据都指向袁党,假如通过合法的体制内抗争和法律解决,国民党未尝不可赢得主动,毕竟民国之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要主动出招,打压国民党尚缺乏合法性。
然而,革命党过于迷信革命,迷恋武力,率先破坏法治,发动二次革命,结果敌强我寡,输了个一败涂地,而且还在舆论之中输掉了道义,形象大坏。因此,国民党在国会里边非常被动,第一大党的位置就让给了进步党。袁世凯乘势要求在尚未立宪之前,先选举总统。
国会中的两党竟然弃约法的程序于不顾,与袁妥协,提前通过总统选举法,将袁世凯推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各派政治势力视约法如“敝屣”,议会民主制所赖以存在的法治基础被自己拆光,无异于政治自杀。
袁世凯在法治的废墟上拿出杀手锏,先是宣布解散“乱党”国民党,然后索性解散国会,毁弃天坛宪法草案(又称“天坛宪草”,即《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3年),建立了赤裸裸的强人威权政治。
04最大的权威是宪法
回头再来看权威之争。在现代民主社会里,最大的权威当然是宪法。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有三种政治统治方式,一种是卡里斯玛(神魅领袖)统治,第二种是传统型的统治,第三种是现代政治的法理型统治。
民国本来应该以制度为中心,以宪法为核心,建立现代的法治,也就是英文里说的Rule of law。但中国人讲到法治,常会和法制(Rule by law)混为一谈。这是一种法家式的统治,中国也有法律,在法家那里,法律不是最高的,法律只是君主统治的工具而已。中国人对法家式的法制特别熟悉,而对真正的法治却很陌生。
民国初年虽然也说要制定宪法,国会也成立了制宪委员会,但实际上每家每派都没有特别把宪法当一回事。当时宪法虽然还没制定出来,但临时约法早已存在,照理说应该按照临时约法办事。袁世凯公然破坏临时约法,结果居然没人抗议。约法只是工具,是否拿来用,要看对当权者是否有利。
中国的政治传统里面,法家视法律为实现统治者意志的工具,而儒家则是“道德为体,法律为用”,法律同样是第二位的。陈志让教授在《军绅政权》里指出,民初政治最核心的价值不是合法或非法,而是有道还是无道。
民初各路军阀打来打去,都认为自己是以有道伐无道,很少有人讲“法”,民初的法律被悄悄搁置到一边。虽然当时也在起草天坛宪法,但这个宪草却是针对特定的人,也就是袁世凯。因为国民党人在宪草委员会中占多数,要限制袁世凯,让总统成为“虚设”,由国会掌握实权。制定宪法不能针对特定的某个人。
这就像我们打牌,要在拿牌之前先制定好游戏规则,这样大家才能都按照这个游戏规则来打。美国政治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里面认为,制定以实现正义为目的的制度,首先要有一个“无知之幕”,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然后来讨论规则的制定。这就像打牌,如果每个人已经先捏着一把牌,再来讨论游戏规则,就不太可能形成公平的游戏规则。
因此,一个能够为大家都能接受的宪法,一定不能针对某个具体的人,必须是普遍公正的。
但是从临时约法到天坛宪草,都预设了特定的目标人物。因此这个宪法无法为袁世凯所接受,当时的舆论对这部宪法也有批评,政治应该是“你活、我也活”的博弈,而不应该是像战争那样的“你死我活”。
民国初年制定“宪草”的政治家们实在太年轻了,平均年龄只有33岁,且三分之一都是学生,原来都是要考科举的,没有什么政治阅历,只有一腔热血。虽然也在日本学了一点宪政的基本知识,但是缺乏政治的历练。
相较之下,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富兰克林等制宪议员平均年龄是43岁,参加独立革命之前,他们都有在英属十三个殖民地长期领导地方自治的经验,既出身草根,又经验丰富。这样一个政治精英群体,因为都有各自的利益,都会发生一时谈判谈不下去,差点崩溃的局面。
这时候富兰克林站出来说了话,“我们暂时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让我们向上帝祈祷给我们以智慧,让我们能够彼此理解。”最后在上帝的指引下,他们相互妥协,搞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且沿用至今的宪法。所以奥巴马才会自豪地说,美国的历史虽然很短,但美国的宪法却是最长的。
天坛宪草一出来,袁世凯根本不当一回事。大家不要以为袁世凯一上来就是想做皇帝,就想破坏宪法。袁世凯善于察言观色,也不想逆历史潮流而动,而是看着潮流顺势而行。民初的宪政为何不能成功,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解释得太简单了,都归结为“坏人”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似乎“好人”当政,政治就会大好。
其实,历史的错误是各家各派共同造成的。
袁世凯的罪恶自不必说,国民党和进步党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那就是过于迷信权力,而忽视了建立宪政的权威。他们只关心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似乎掌握了权力就拥有了一切,但却忽视了,即使好人当政,若这个权力不受制度约束的话,好人也有可能作恶,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人。当时的人很少考虑到宪政的设计,应该是用权力来限制权力。当时的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进步党党魁梁启超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也忽视了这一点。晚清的时候梁启超与革命派有一场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核心之一,就是对革命的分歧。
革命派这一边的汪精卫、胡汉民都太年轻,满脑子的法国大革命思想,认为革命一成功,一切都解决了。而梁任公饱读历史,从法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之中看到,革命之后若不立宪,就会产生多数人的暴政。清廷“十九条信约”出来以后,梁启超认为这虽然不是最好的制度,却是当时最适合中国的制度,但是没有人听他的。
等到革命成功,回国后投身政治,他便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提出要弘扬国权,搞总统制,联合袁世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当他在政治里面跌打滚爬的时候,忘记了其一生追求的核心目标——宪政。立宪派养大了老虎,却忘记把老虎赶进笼子,最后间接促成了袁氏称帝。
到这个时候,梁启超方醒悟过来,重新回到立宪的立场,他明确宣布:“吾侪平昔持论,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自此之后,他关心的是权力的制衡和政府的管理以及一套有序的秩序。他相信,只有宪法秩序才能给予政治斗争有序的空间。
回顾这一段历史,民国初年,从革命一开始发生,就注重权力,无法建立一个新的民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
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可以从这段历史中总结出两条经验。
第一条就是,改革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成为革命的替代物,也可能成为革命的诱发剂,要避免改革变成革命,改革一定要彻底,改革不能倒退。第二条,新的制度转型,最重要的是制度建设本身。这就是辛亥百年留给我们的一个沉重的教训,值得我们今天来反思。
赞(31)